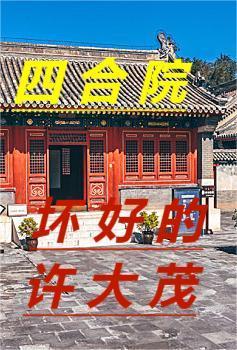恋上你看书网>会脱单byLlosaTXT > 第66頁(第1页)
第66頁(第1页)
聞笛迅捂住了對方的嘴,火冒三丈:「你他媽亂說什麼!」
男人垂眸看著他,再開口時,聲音恢復了平常的音量,悶在聞笛的手裡,模糊不清:「我總結的不對嗎?」
聞笛意識到他和何文軒的對話全被別人聽去了,惱羞成怒:「誰被甩了?我甩的他好不好!」
男人毫無反應,聞笛的牙都快咬碎了。如果不是那七百美元——以及他不認路,以及男人體格健碩,一看就打不過——他肯定跟男人拼個你死我活。
他什麼眼光,從酒吧烏央烏央的gay里挑出一個最氣人的!
男人握住聞笛的手腕,把他的手拿下來:「可以走了嗎?」
聞笛仍然瞪著他,似乎是氣到極點,把喉嚨都堵住了。他就拽著聞笛的手,轉身往主街的方向走。聞笛氣糊塗了,居然沒反抗。
走了三個街區,聞笛才憤懣地說出聲:「你這個人,是不是這輩子沒遇到過什麼挫折?」
男人不知道是沒聽見還是懶得回答。
「一看就是,」聞笛說,「一點同理心都沒有。」
「我只是不覺得喊出來能有什麼幫助。」是懶得回答。
「拉倒吧,就是沒有,」聞笛說,「就算有,能有我這麼丟人嗎?」
過了一會兒,男人才說:「不就是男朋友要結婚嗎?」
「我靠,」從別人嘴裡說出來,殺傷力更強了,聞笛捂住胸口,「你知道我過去五年是怎麼對他的嗎?」
回程的路太漫長,足夠他從軍訓送水說起,一路講到生日驚喜。聞笛越說越覺得自己像個冤大頭,掏心掏肺了五年,在別人眼裡就是個當情人有餘,當配偶不足的實用保姆,食之無味棄之可惜。
男人沒有打斷他,直到主街的霓虹燈再次映入眼帘,聞笛結束了五年血淚史,才開口說:「我挺羨慕你前男友的。」
「草,」聞笛說,「不會安慰人就別說話。」
當然,男人怎麼可能聽他的。「遇到一個全心全意愛自己的人,這是多稀有的概率,」男人繼續說,「他竟然這麼隨隨便便扔掉了,丟人的是他,跟你有什麼關係?」
聞笛啞然。他原本預備著男人冷嘲熱諷,沒想到對方突然來這麼一出。也許是之前男人的表現拉低了期望值,兩相對比,他居然非常感動:「沒想到你也會說兩句人話。」
男人尖銳地看了他一眼。
「不過,」聞笛說,「這不是我覺得丟人的地方。」
男人啞然。從剛才開始,這人的詛咒滔滔不絕,把前男友噴成豬狗不如的畜生,難道不是因為結婚嗎?
「你父母是做什麼的?」聞笛問。
這問題莫名其妙,男人還是回答了:「都是大學教授。」
聞笛點點頭,感嘆:「真好,別人問起父母的職業,你肯定回答得很爽快吧。」
男人覺得這話奇怪:「你父母是做什麼的?」
「開早點攤的。」
「你不是也很爽快嗎?父母的職業有什麼關係?」
「沒關係啊,」聞笛說,「21歲的我覺得沒關係,但16歲的我覺得有天大的關係。」
他頓了頓,大概是想起了不好的回憶,嘴角耷拉下來:「我跟何……我前男友剛在一起的時候,他跟朋友出去玩,我也去了。他周圍都是什麼公司高管、老闆、總工的兒子。吃飯的時候,他們問我家裡是做什麼的……」他咬了咬口腔內壁,「我說我爸媽都是醫生。」
男人沒有對此發表意見,重做回沉默的聽眾。
「之後,為了圓這個謊,我查了很多醫生的資料,我爸媽上的哪個大學,主攻什麼科,擅長什麼手術,周幾排班,遇到過什麼麻煩的病人,我都編好了,比寫小說還詳細,」聞笛說,「挺諷刺的,上高中之前,我還以為我是全天下最愛父母的孩子。」
之後的話有些難以啟齒,聞笛用手搓了幾次衣角,才接著說下去。
「我自以為我編的故事天衣無縫,結果我撞破前男友結婚之後,他談到了申請國外大學的事,」說著說著,聞笛雙手抱住腦袋,「他早就知道了!高中的時候就知道!這麼多年,他就看著我表演一個醫生的孩子,背地裡不知道和朋友們怎麼笑話我,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?」
男人不知道如何作答,只能搖了搖頭。
「一切都毀了,」聞笛說,「連最後那麼一點值得留下的記憶,都沒有了。」
比如有一年他生日,何文軒請他去高檔餐廳吃飯。他們坐在大廈頂層的落地窗旁,滿城燈火就在腳下,燈光音樂都美的讓人迷醉。只是從落座開始,一切就格格不入。
聞笛坐下去的時候,自己用手把椅子拉了回來。何文軒在對面提醒他不用動,他才注意到後面的侍者。侍者倒酒的時候,他本能地把酒杯舉起來,讓杯口湊近酒瓶。侍者來收盤子,他把自己的空盤子遞過去,放在托盤上。
何文軒一直在看著他,他問怎麼了,對方笑著說:「覺得你很可愛。」
當時覺得滿是初戀的甜蜜,現在回想起來,那個目光可能不是欣賞,是覺得丟臉。
「你知道這種感覺嗎?」聞笛問,「你突然發現一個人和你想像中不一樣,然後你想起過去那些美好的回憶,發現它們全被推翻了。」
男人突如其來地開口了:「我知道。」